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《731》《南京照相馆》《东极岛》等影片公映,为重拾战争记忆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真相提供了银幕叙事方式。在日本的文化工业中,影像却展现出日本社会对战争暧昧、分裂的记忆叙事,使得美化军国主义、掩盖战争责任等问题浮出水面。
日本为何会走上军国主义的“暴走”之路?当代日本将走向何方?思南读书会上,历史研究者、《暴走军国:近代日本的战争记忆》作者沙青青,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、《“无责任”的帝国: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(1895-1945)》作者商兆琦为读者一一解读。两本新书均由上海三联书店推出。
 分享会现场
分享会现场
《“无责任”的帝国: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(1895-1945)》以日本近代的50年为切片,商兆琦坦言:“写这本书时,感觉日本这50年像一个轮回。日本就像一个‘穷小子’,发了大财,积攒了很多财富,在二战和侵华战争中挥霍一空。这50年就像中国人说的黄粱一梦,1895年甲午战争这个起点非常重要。就像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所写,日本这50年的扩张就像小孩吹气球一样,吹得越大,越容易爆炸、破裂。”
 商兆琦
商兆琦
沙青青认为,“无责任”是解读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失控、暴走的一个很好的视角,这一点可以从近代以来日本畸形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展开。“1890年日本制定的所谓明治宪法第11条和第12条规定,天皇是日本陆海军的统帅,由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和常备军数量,这意味着军事指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天皇,日本的内阁制政府总理大臣无权处置军事事务。这就导致日本和其他现代国家不一样,其军事体制和政府是平行的,两者从权力关系而言都处于天皇架构之下,是平行关系,这是导致日后政府和军事部门之间冲突的原因。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,侵华战争扩大之后,军事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僭越政府部门,政府为抢夺事态主导权,与军事部门竞争,为取得政治话语权,互相比赛谁更激进。”
 沙青青
沙青青
“讨论日本为何一次次走向战争之路,我们会特别强调其军队,尤其是陆军在其中发挥的恶劣影响。天皇是名义上的权威象征,但没有实质的权力,因为日本实行的是绝对君主制与立宪君主制的结合,在垄断权力时,天皇表现为绝对君主,但为了保护天皇,为了让其规避责任,又套上了立宪君主的外壳,显得十分扭曲。”商兆琦说,这就是日本“无责任”体制的重要原因,“天皇在行使权力时,什么都可以做,在承担责任时可以躲起来。”
“‘无责任’的体制,一方面把法律上的权威赋予天皇,但天皇又不承担实际的责任,导致找不到到底谁来最终负责、裁决。我们谈到二次世界大战,谈到法西斯、轴心国,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罪魁祸首,比如纳粹德国的希特勒,意大利的墨索里尼,日本呢?是昭和天皇还是东条英机或其他人?似乎找不到可以跟希特勒、墨索里尼等量齐观的罪魁祸首,只能找到战犯集团,这是日本传统文化在二战以来、法西斯时代的具象体现。”沙青青说,就像一辆上足马力的战车冲向悬崖,所有人都找不到刹车。
沙青青提出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点,日本对外侵略扩张,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进入了新阶段,“九一八”之后,打开了一个危险的闸门,与此同时,日本国内政治迎来一波又一波血雨腥风的动荡,越来越多出身草根的青年军人,以激进方式发动军事政变威胁或暗杀政府官员,“整个1930年代,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和内部政治的张力,微妙地嵌套在一起。此外,20世纪30年代初,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社会萧条、经济衰败的状况。这种状况之下,各种思潮开始浮现出来。如果你回头看,整个30年代,日本以军国主义的状态,通过饮鸩止渴的方式解决国内外的问题和矛盾。”
1944年底,日本国内,无论是军方、政府还是民间,其实都已经深刻地感受到战争难以为继,但没有一个集团愿意率先提出投降的意见,直到1945年4月,铃木贯太郎出任首相,在其推动之下,才开始迈向所谓投降过程,即便如此,整个过程曲折而缓慢。在沙青青看来,日本的投降过程仍然延续着“无责任”的状态,日本也有学者写过相关论著,称其为“迟来的圣断”,意思是天皇所谓的投降命令,来得太晚了。
“历史研究者要走出书斋、走向社会,向更多人普及历史知识和研究心得。”在思南读书会的这场分享,是近期沙青青和商兆琦联袂带来的第二场活动,商兆琦感慨,“面向公众传递研究成果,是文科研究者重要的社会责任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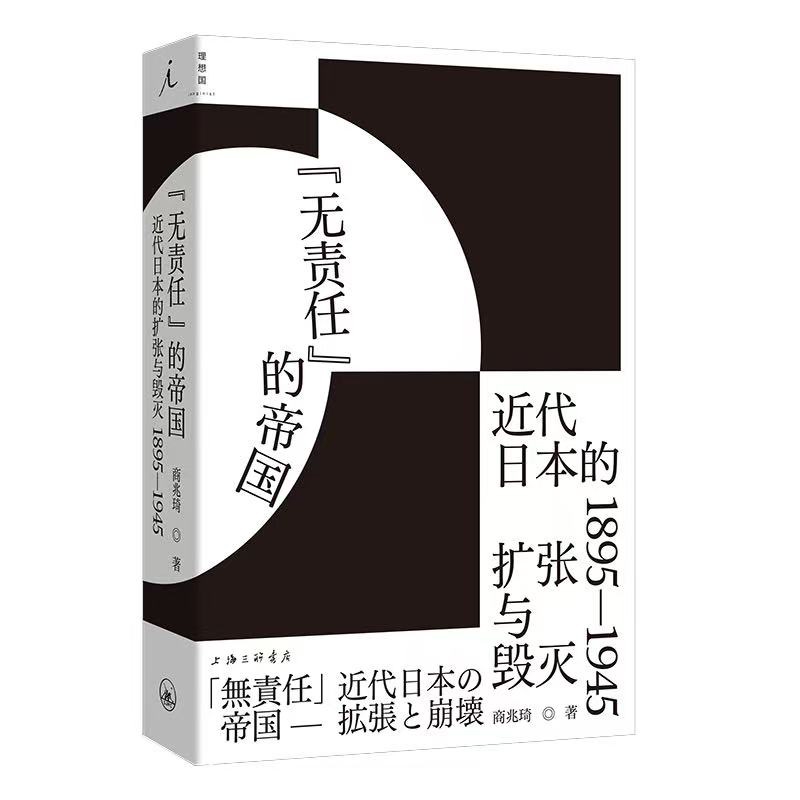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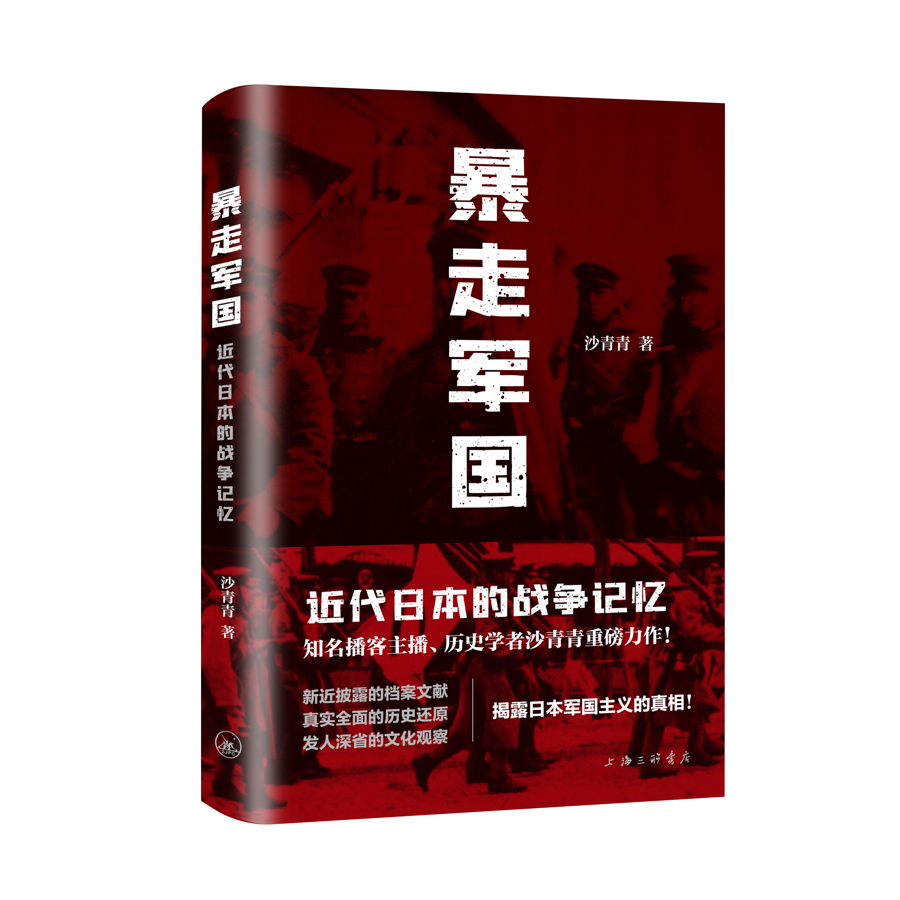
广源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